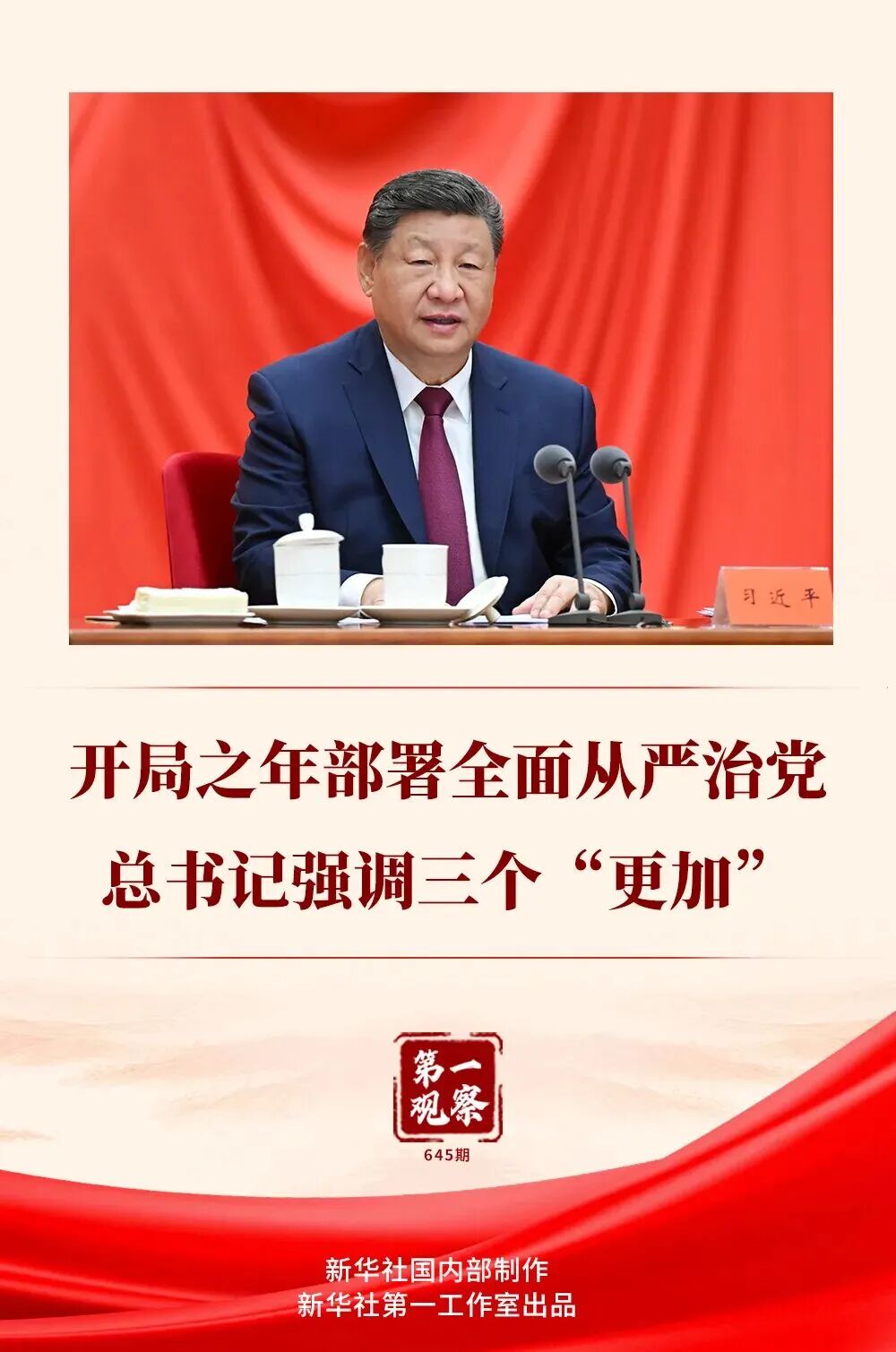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正当全国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如火如荼、风起云涌的时候,封闭落后的康县人民还在懵懂中承受着亘古认命的灾难,他们苦于世道的不公和命运的不济,却不知道如何团结起来,用共同的力量抗击暴虐、获取自由。就在这国家内忧外患、民族悲苦危亡、社会动荡不安、民众麻木愚蒙的关键时刻,一支严整威武的神勇之兵走进了偏僻的陇南大山,这支军队在历经康县的短暂时间内,发动群众,启迪民心,镇压恶霸,赈济百姓,组建地方游击队,成立苏维埃政权。从此,古老的康县在沉睡中苏醒,红军及其响亮的名字深深地印在了康县人民的心里。
世纪曙光
1936年是康县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康县人民初次见到了自己的军队,感受到了民主革命带来的福祉。9月1日,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研究制定了成(县)、徽(县)、两(两当)、康(县)战役计划。8月,红二方面军根据中央和中央军委“东出甘南和陕西南部,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凤县和宝鸡地区,从右路拖住胡宗南尾巴,配合一、四方面军进行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发布了“乘陕甘敌人分兵据城的弱点,透过其封锁线,打击成县、徽县、两当、凤县、略阳、康县之敌,而袭取之,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为目的的“成徽两康战役”基本命令。10日,红二方面军总部决定分三路纵队行动:二军团六师为右路纵队,9月12日从西固(今宕昌)出发,向东南康县方向行进;二军团四师和三十二军为中路纵队,11日由闾井出发,向成县、徽县进军;六军团为左路纵队,11日由马坞出发,向两当、凤县进军。红二方面军副政委关向应,六师师长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等同志率领六师十六、十七、十八三个团执行“成徽两康战役”命令,9月12日从西固出发,经西和进入武都的隆兴、甘泉、佛崖,18日进入望关,由此开始了红军长征的康县之旅。这天,阴雨初晴,大地迎来了久违的阳光,部队中午来到长坝,适逢集日,集市上的人看到有队伍到来,个个神色慌张,走在前面的红军挥手高喊:“乡亲们,不要怕,我们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他们在集市上公买公卖,秋毫无犯。在途经何家庄时,有两个红军战士来到路边王金玉家,要求用自带的面粉换几个馍馍充饥,王金玉见是当兵的来了,心里既仇恨又害怕,便说:“你们想吃拿就是了,还给啥面哩。”红军战士以为老乡不愿换,便饿着肚子走了。贫苦农民王玉生目睹了红军在长坝的一举一动后,很受感动。他主动担任向导,带红军到分路口菜子垭梁,临别时红军还给了钱以作酬谢。
下午部队宿营在巩集,当地群众听说有部队要来,大多数人都躲藏了起来,村里只有老弱病残的人留守。红军打开了地主李瑞云家的粮仓,把存放的小麦和大米分给了穷人。他们帮助群众关好躲藏前未及时关上的门窗,打扫干净村落卫生,给老百姓家里的水缸装满了水,晚上全部露宿在村头草铺上。红军走后,大家回来一看,自家东西完好无损,院落干净整洁,用了的粮食、柴草都写有欠条。敬坪一位老大娘给红军送了一背篼豆角菜,第二天发现灶上放了几个铜板,她兴奋地感叹道:“莫非世事变了,活了半辈子还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队伍。”
19日,红军由巩集出发,沿古大道蔡家沟经悬崖小径水洞砭、翻越纵横险峻的毛垭山,一路攀岩缚葛,披荆斩棘,循周家沟小溪直逼康县县城云台,侦察部队行至小沟门与随众躲藏的云台学生袁治邦相遇,袁治邦很快被红军说服,并做向导带部队进城,急问口令,并用手电光探视,红军立即用密弹作答,接着骑兵部队迅速绕南河向东门包抄过去,保安队难以抵挡,弃城而逃,红军顺利进城。
古 城 爝 火
红军的到来,就像漫漫长夜中的一团爝火,驱散了黑暗,给这个沉寂腐朽的地区带来了希望和生机。红军进入云台后,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红军来了要共产共妻”、“赤匪要杀人抢粮”等谣言影响,大部分群众心存戒备,离家躲藏。经过长期艰难征战和长途跋涉,此时的红军已经身体虚弱,衣衫破烂。大多数人面黄肌瘦,身着长衫短褂,多以草鞋树皮裹脚。但他们仍然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贺龙总指挥提出的群众工作基本纪律。在未能得到群众信任的情况下,即使挨饿受冻,也不擅自动用群众财物,还处处设法帮助群众。红军给流落街头的乞丐焦管管分给衣物和干粮,并向他讲解革命道理。听了红军所讲,焦管管茅塞顿开,深受启发,便找到了在群众中有威望的贫苦农民崔怀清,一起把出外躲藏的群众叫了回来。师长贺炳炎住在中街农民李春生家和群众谈心,从中了解康县的县情以及老百姓的思想生活状况。当得知红军的到来把学生也吓跑的情况后,就立即派袁治邦等人说服群众,动员教师、学生回校上课。
在稳定群众情绪的基础上,为了完成党中央的战略计划,扩大红军在更大范围内的工作成果,师部决定,主力部队十六、十七、十八团由关向应、贺炳炎、廖汉生等率领继续向略阳东进,十七团留康开展苏维埃活动及扩充红军工作。基于对康县敌我形势的考虑,师部决定加强十七团的领导力量,派师政治部主任刘型和特派员王金甲带一侦察班帮助十七团工作。20日,十六、十八团先行离开康县。留康十七团也立即投入工作,刘型、王金甲及时召开团政委、团长、参谋长会议,会上传达了师部的两条命令:一是命十七团在康县掩护大军过江,并扩充红军;二是各营分散驻防。一营由刘型、王金甲带领驻康县县城,二营由团政委段远武带领驻窑坪,三营由团长蔡炳贵、参谋长苏绪庚带领驻陕西略阳郭家坝,会后各营奉命到各地驻防。留康红军以云台为临时根据地,张贴标语,登门造访群众,组织演讲会,和群众交流谈心,启发引导群众区分敌友,认识时局,提高觉悟。广泛深入的宣传活动,消除了群众的疑惑,红军的行动也赢得了广泛的理解和支持。躲藏的人很快返回村里,帮助红军筹集粮草、衣物等。不少人腾出自家的房屋、热炕让红军住,拿出自己的口粮让战士们吃,军民互敬互爱,很快融为一体。
在普遍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红军着手组建地方革命政权,领导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在红军的主持下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康县苏维埃临时政府,推选崔怀清为主席,孙占奎、李殿臣、焦管管为委员。会后,他们杀猪宰羊,酒宴庆贺,军民共享胜利喜悦。在苏维埃临时政府领导下,广大群众一面打富济贫,打开地主张守礼家的粮仓,把粮食分给穷苦农民;一面发动青年参军,壮大红军队伍。驻窑坪红军也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在关帝庙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窑坪苏维埃临时政府,帮助群众组建了地方游击队。一时云台一带掀起了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武装革命热潮,仅一个星期时间,要求报名入伍的青年就达数百人,并筹集募捐了大批军需物资,部队在补给中得到了休整。当时的情景正像一首民谣中所唱的:“红布条条胸前挂,一把马刀腰间挎,跟上红军闹革命,抗日救国打天下。矛子磨的锞灿亮,马刀飞快映红绫,四路八乡打土豪,锦绣河山遍地红。”
战 略 转 移
当留驻康县红军领导的农民武装斗争如燎原之火迅速扩展蔓延的时候,革命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张国焘破坏了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制定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龟缩在武都窥视我红军去向的国民党中央陆军第三军从武都出发,偷渡犀牛江向成县进犯。红十八团奉命由关向应、廖汉生率领,欲从白水江出发急进成县,与中路军配合阻击成县五龙山敌军进城。此前离康的红十六、十八团继续在白水江一带开展苏维埃运动。为了应对复杂的敌我形势,破坏敌人把一、四方面军压倒在甘陕大道以北,把红二方面军隔断在渭水以南的企图。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根据中央“红二方面军撤离成、徽、两、康地区,渡渭水北上”的指示精神实行转移。十六、十八团摆脱敌军围困在即,在争取时间渡过渭水时,行动仓促,对留康红军第十七团未来得及收拢,与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驻云台红军全体指战员得知情况后及时分析了形势,决定实行战略转移。9月25日,红军与云台群众依依惜别,从云台出发和窑坪红军一起向郭镇进发,全团在郭镇会合,谋求新的行动计划,以图尽快赶上大部队。
悲 壮 觅 途
红军转移后,国民党康县政府官员立即反扑回城,对新生红色政权进行疯狂镇压,他们撕毁红军张贴的标语,追捕杀害我苏维埃临时政府成员和农民进步人士。在云台,孙占奎、焦管管被先期捕杀;李殿成在追捕中走投无路,服毒身亡;崔怀清四处躲藏,一月后被抓回县府,剥光上衣,背上火香,游街示众,在脊背被烧焦糜烂,身体不能支持的情况下投进监狱,后因兽医出身的崔怀清治好了县长王肇南的坐骑才幸免一死。从此,红军领导的康县苏维埃农民运动进入了低潮。
红十七团从云台、窑坪撤离后,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一时陷入了茫然无存、孤军无助的境地,随时都会受敌围困。为了走出困境,团部在陕西郭家坝召开了全团大会,分析了形势,统一了思想。决定绕开国民党和土匪控制区,以康县南部一带深山密林作掩护,向岷县方向行进,继而寻找红军主力。部队在郭家坝出发时找了当地一人作向导带路,全团将士满怀着对胜利曙光的期盼,在云遮雾罩的大山中行走了一整天,当行至略阳阳平关苍社沟时,发现被领到了国民党部队驻地,他们立即除掉了向导,及时绕过伏击圈,部队才幸免遇难。接着改道向两河、铜钱方向进发。时值秋雨连绵,云雾弥天,部队翻山越岭,涉溪绕河,几乎是盲目行进。进入清河林区后,复杂的地势和茫茫林海更使红军将士屡屡迷失方向。红军迂回多日才跳出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到白洋滩时,许多红军战士已是伤病加身,战士们相互勉励,彼此照顾,绕过可能遇到的匪患,经枫香岭低垭子梁到了铜钱坝。在经过罗家坪时不幸遭遇了地方武装李希业的偷袭,一红军战士受伤,部队且战且行,到了三河坝,当地豪绅吕占鸣依赖于碉堡挡住了去路,师政治部主任刘型当机立断,亲自指挥迎敌,但终因碉堡坚固未能攻下,部队以保全力量为重,拖着伤病员及时撤离,沿铜钱河继续上行,经吕家坝、秧田坝、石碑岭、中坝、松树坝、上曲河、店子、豆坝、老虎垭,辗转来到碾坝,部队在袁家沟经小憩休整,决定去望子关沿古道绕敌前行,不料有消息称,望子关有敌人把守,便又抄山路行进两日,到了一个据说距岷县九十里的三岔河,悉知红军已离开岷县北上。此时的十七团将士已身心疲惫,士气低落。在既无信息,又缺乏补给的情况下,团领导决定让部队暂时隐蔽山林,待探明消息再作打算。十七团官兵选择了沿路返回的路线。在途经佛崖时陷入敌人的伏击圈,部队同遭重撞,刘型身负重伤。战士们扛着武装,抬着伤病员,继续缓慢行进。又过了四、五天时间,刘型的伤情日渐加重,生命危在旦夕。战士们互相鼓励,加油,绕过了一个个险关要隘,进入一个不知名的林区,刘型这位坚毅刚烈、驰骋沙场的湖北籍铁血男儿终因高烧昏迷,伤情恶化而长眠于陇南南部的万山丛林之中。
刘型的牺牲给红十七团造成了惨重的损失。随着优势兵力的不断减员和伤病员体质的下降,余部官兵的情绪异常低落,艰难的行程使他们感受到离开大部队的孤独与无助,在茫茫的山林里,战士们几乎得不到给养,为了活命,有的士兵偷吃田地里的玉米棒子,却激怒了山民,被误认为残匪,遭到围攻追击。在一个宿营地又遭遇了地方武装王吉华的袭击,兵员死伤惨重,十七团手枪队被打散,全团仅余二、三十人,他们再次转移营地,最后到了一个三面陡壁悬崖,一面临水的所在,经打听得知是嘉陵江边的阳平关,团部在此安营数日,最后弹尽粮绝,几乎无路可走,团领导基于余部求生和保存实力考虑,同意战士们分散自谋生路的请求。从此,红十七团隐没消失在陕甘交界康县南部的大山深处。(作者:高振宇)